下载地址
可按照索引号(标题前面的s+数字)在我的资源盘内找到相应的资源
内容介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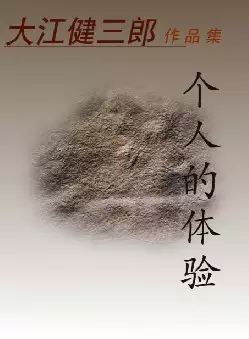
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
王中忱
1994年12月7日,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为这一年度
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登上瑞典皇家文学院讲坛的时候,心
情肯定不很平静。获奖确实使他喜悦,但也打破了书斋的安
宁。为了躲避新闻记者接连不断的骚扰,他甚至不得不有意
弄坏电话。
①不过,从东京到斯德哥尔摩,总有许多仪式需要
履行。和以往的一些杰出前辈一样,他要在这里发表受奖演
说。
大江的目光投向了距离讲坛遥遥万里的故乡。于是,四
国岛上名不见经传的大濑村(现名内子町大濑),就成了《我
在嗳昧的日本》这篇著名演说的开场白。大江并非突然泛起
10个人的体验
①参见大江健三郎1994年10月17日在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
的“日本研究·京都会议”上的讲演。
了乡愁,至少在两个月前,获奖消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
来时,他便开始酝酿这篇讲演辞。而比这稍早一些时间,大
江曾经“在北欧谈日本文学”,那时,他也说起自己的故乡。
①
显然,故乡的土地始终牵系着大江的心,与大江的文学世界
丝缕相连。
大江经常把故乡称做“峡谷里的村庄”。大濑确实藏在山
谷里,村前有小田川河流过,四周则环绕着茂密的森林。大
江在这里长到15岁,“峡谷村庄”经验可以说就是他孩提时
代的经验。大江后来的创作表明,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,会
在作家的文学活动中持久不断地回响。诚如大江自己所说:我
曾屡屡描述森林里的孩子的奇异经验,即或人家认为我是受
森林经验的恩庇而成为小说家的,我也毫无异议。
②但“峡谷
村庄”不仅为大江的创作提供素材来源,它还时时跃入大江
11个人的体验
①
②参见大江健三郎的小说《占梦师》。
参见大江健三郎《在北欧谈日本文学》,1992年10月;此文和大江的另
一篇讲演《不再封闭的日本人》(1993年5月)谈到的内容,与《我在暧昧的日
本》多有重合,几乎可以视为后者的雏形。
虚构的世界,构成作品内在的时空。而虚构文本(test)里的
“峡谷村庄”自然不限于现实中的大濑村形成某种对应,在文
本内的各种语境(contest)里,它指涉着多重复杂的内容;从
这样的意义说,森林-峡谷村庄无疑是解读大江作品的一把
钥匙(keyword)。
“峡谷村庄”作为虚构的空间,最初出现在中篇小说《饲
育》里。《饲育》是大江创作中少有的一部直接描写战争时期
生活的作品,在战后日本文学的同类题材作品中也属异例的
存在。“峡谷村庄”这一情境的设定,使故事发生的空间带有
某种封闭自足的乌托邦色彩,山村孩子的视点,更加重了这
里的牧歌气氛。尽管有战争的消息传来,甚至有敌方的飞机
在空中盘旋,但对于山村孩子来说,这一切非但构不成恐惧
和危险,反倒增添了新鲜的乐趣。最后,导致乌托邦解体的,
既不是战争,也不是那个被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,而是村庄
里大人们的支配意志与暴力行为。在小说结尾,当“我”的
手指和黑人士兵的头骨一起被“我”的父亲打碎的时候,也
12个人的体验
意味山村孩子的童年乐园从此失去。“我不再是孩子了。”这
是“我”获得的启示,也是小说中俘虏兵故事与山村孩子的
成长故事交融起来的接点。“峡谷村庄”由此而转换为山村孩
子举行成年典礼的仪式性空间。
《饲育》里关于“成熟”的启示,从某种意义可以看做是
大江创作本身的隐喻。《饲育》以前,大江已经以《奇妙的工
作》(1957)、《死者的奢华》(1957)等作品引起文坛注目,尤
其是《死者的奢华》,甚至成为日本纯文学界最看重的芥川文
学奖的候选作品。但大江的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,确实非
《饲育》莫属。这篇小说发表当年(1958)即没有争议地获得
了芥川奖,从而促成大江从“学生作家”顺利地转为职业作
家。就文学创作而言,大江也可以充满自信地宣告:“我不再
是孩子了。”《饲育》以后,大江仍然探索“成熟”与“失
乐”这一母题。《感化院的少年》(1958)和《迟到的青年》
(1960)等作品里,仍然泛着童年乐园失去的忧伤,但山村青
年渴望的,显然是远方都市的冒险,他们希望在那里验证自
13个人的体验
己的成熟。“峡谷村庄”的隐喻内涵发生重要变化,始自大江
于1967年发表的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》。这是一部规模宏大
的长篇,在历史、现实、传说、民俗交织而成的繁复结构里,
“峡谷村庄”首先作为人物“回归的场所”而登场。小说主人
公根所蜜三郎、根所鹰四都是从山村来到现代大都市的青年,
作品开端,两兄弟都正陷在彷徨无路的精神危机中。鹰四曾
积极参与1960年反对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学生运动,运
动失败后,到美国放浪度日。他渴望结束浮萍般的漂泊,寻
找到心灵的归宿地;蜜三郎则始终是学生运动的旁观者,他
陷入的是家庭生活困境(孩子先天白痴,妻子酒精中毒)。兄
弟二人的人生观念虽然颇不相同,但在返回故乡,开拓新的
生活这一点上,却获得了共识。如果说,在大江此前的作品
里,“峡谷村庄”主要意味着“丧失”,那么,在《万延元年
的足球队》里,“峡谷村庄”则是根所兄弟寻找自我、寻找心
灵故乡的空间。大江曾说:小说主人公的家族姓氏“根所”,
14个人的体验
意思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们灵魂的根本所在。
①作家关于家
族历史与灵魂根源的解释,可以说明根所兄弟的“寻找”由
现实深入到历史层面的原因。鹰四通过想象重构自己的曾祖
父之弟、万延元年(1860)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神话,明显
是为自己组织村民的行为寻找历史认同的依据(identify)。而
鹰四与蜜三郎的对峙,则与其曾祖父辈的兄弟冲突形成呼应。
最后,鹰四也像他的祖辈一样走向了毁灭,但他的死亡却促
动了蜜三郎的转变。蜜三郎终于意识到,鹰四是坚忍地承受
心灵地狱的磨练、顽强探索超越心灵地狱、走向新途的人;于
是,他勇敢地接回自己的白痴儿子,收养了鹰四的孩子;从
鹰四的人生终点,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。“峡谷村庄”就这样
成为提供“再生”可能的理想空间。
在大江的文学世界里,“森林”与“峡谷村庄”几乎是可
以相互置换的意象。作家曾说,他所理想的乌托邦,就是
15个人的体验
①大江健三郎:《在北欧谈日本文学》。据作家说,这一姓氏是根据冲绳语
里的一个词汇确定的。
“我的故乡那里的森林”,“森林峡谷里的村庄”。
①和“峡谷村
庄”一样,“森林”在大江的作品里,常常作为人物的“再
生”之地(如《同时代的游戏》,1979年),或者核时代的隐
蔽所(《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》1968年)而出现。在“森
林”的延长线上,无疑还矗立着“树”的意象。大江的作品
里关于树的描述俯拾皆是,几乎达到偏爱程度。他的“雨
树”系列之所以把“树”作为“死与再生”的象征,他的最
后一部小说之所以仍然以树为题(《燃烧的绿树》),都不是
偶然的。大江说,树是帮助他跃入想象领域的旅行器械,是
他“接近圣洁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的媒介。”②
应该说,如果仅仅把“森林-峡谷村庄”作为理解大江
作品文本的关键符码,那是不够的。森林-峡谷村庄与大江
的文学世界有着更深刻的联系,它对于大江的独特认知方式
16个人的体验
①
②大江健三郎:《作为旅行器的树木》。
大江健三郎:《寻访乌托邦 寻访故事》。
及小说方法的形成,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。大江回忆说:
“30岁的时候,我第一次访问冲绳和美国,并在那里短暂停
留。冲绳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质,以及其
与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纵向垂直的秩序相并行的……异文化
共存结构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以此为媒介,我得以重新
发见森林里的村庄的文化结构。”①
相对于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,大
江看到了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的多样、丰富、开放的生
动形态。这一发见直接促成了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》的创作,
作家说:“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,即是我渐次意识
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,亦即
边缘文化。”②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,大江则明确提出了“边
缘-中心”对立图式,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讨论。他
认为,“从边缘出发”,是小说整体地表现现代世界、把握现
17个人的体验
①
②大江健三郎:《在北欧谈日本文学》,1992年10月。
大江健三郎:《为日美新的文化关系而写》,1992年5月。
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,“必须站在‘边缘性’的一边,而不
能顺应‘中心指向’的思路。”①
大江所说的“中心指向”,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位置的
主流意识形态。他清醒地看到,在现实中的日本社会,即使
是偏远的山村,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起着支配作用。他
认为,最重要的对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,是通过文学语言,
创造出真正立于边缘的人的模型(model),从而使人们的认
知结构化,获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。
②
“边缘人”当然不能简单从地理学意义上理解,大江主要
是从社会-文化结构的视角为“边缘”定位。他认为,在社
会-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,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
方,基本处于边缘位置;而其中受灾致残者,更处于边缘的
边缘。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,边缘人的声音无疑被压抑
18个人的体验
①
②参见大江健三郎《小说的方法》“走向边缘,从边缘出发”章。
大江健三郎:《小说的方法》,1978年,岩波书店。据该书“后记”,大江
“边缘-中心”模式的提出,与阅读山口昌男的《文化与两义性》(1975),接触结
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理论有关。
着。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和创造,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出来,
自然为既成的稳定的社会-文化秩序引入异质因素,使人们
习以为常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,从而引发出对既成社会-文
化结构的质疑与新认识。
①
从上述意义上说,《广岛札记》(1964)、《个人的体验》
(1964)无疑都属于“从边缘出发”的创作。尽管大江提出
“边缘”概念远在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。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
面说明,大江用“边缘-中心”图式讨论小说方法,固然不
无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,但同时也是他自我体认、探索思考
的结晶。《广岛札记》汇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数访广岛的所见、
所思,明晰显示出其“从边缘出发”的指向,是透视现代社
会乃至现代文明,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。在这样的视野里,广
岛原爆的受害者们的位置与意义即发生变动,他们不仅让人
触目惊心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,其自身还蕴藏着治愈核时
19个人的体验
①参见大江健三郎《小说的方法》“步向边缘,从边缘出发”章。
代社会疾病的力量。
《个人的体验》与《广岛札记》的题材、文类绝然不同,
但作家却常常把这两部作品相提并论。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两
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几乎重合,更主要的在于两者间确有许多
内在的相同。原爆与畸形诞生,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
灾难,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,人该怎样生存?广岛原爆受难
者和残疾儿的父亲鸟面临的是同样的课题。残疾儿童的出生,
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,照射出现代人心灵的残疾,最后促
成鸟走过心灵炼狱,获得精神上的新生。
《个人的体验》常被视为关于人的“再生”的故事,但关
于小说结局鸟和残疾儿共获新生的处理,却不无异议。著名
作家三岛由纪夫即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,这一事情后来甚
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小说里(《写给那令人眷念的年代》)。据
作家笠井洁分析,三岛的不满,主要在于大江把人物认识与
行为二律背反式命题,通过鸟的突然转变,变魔术似的突然
20个人的体验
解消了。而这一命题,恰是三岛苦苦探索不得解脱的。
①如果
确如笠井所说,那么,三岛的批评可谓击中要害,但纵观大
江的全部创作,也可以看到,《个人的体验》的结局,并不是
大江关于“再生”问题思考的终点。毋宁说,自《个人的体
验》起,一直到目前正在写作中的最后一部长篇,大江都在
苦苦探寻人类“拯救”“再生”的途径。在“雨树”和《新人
呵,醒来吧》(由《天真之歌,经验之歌》等构成)两个系列
作品里,清晰留下了大江探寻的轨迹。不过,《个人的体验》
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被普遍接受,被新闻媒体广泛传播,而
大江后来的探索则很少被一般读者注意,确是不必讳言的事
实。书有书的命运,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吧。
大江是一位方法意识极强的作家。他不仅认真研读俄国
形式主义、结构主义以至巴赫金的文学理论,而且,自己还
21个人的体验
①参见笠井洁、柄谷行人的对谈:《关于“结局”的想象力》,《国文学》杂
志第35卷第8号。
专门写作了《小说的方法》等理论著作。但是,大江并不沿
着内容A形式的思路去考虑文学的方法问题,他所说的“方
法”,并不限于形式、技巧层面,而是贯注着米兰·昆德拉所
说的“小说精神”,与“小说精神”融为一体、互为表里。作
为小说方法的“边缘意识”,既与大江的小说构成方式密切相
关,又体现了他认知世界的方式,甚至凝结着他的人格追求。
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,大江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物,成为
新闻报道的中心,日本政府也按惯例拟议授予他文化勋章。
但大江表示拒绝。他说:那勋章对我来说,会像寅次郎
穿上礼服一样不般配。
①寅次郎是一部系列电影里,一个幽默
风趣的小人物形象。大江提到他,表明了自己的平民情趣和
立场,也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“边缘意识”。他拒绝主流文化
意识形态的同化,“走向边缘”;当然,是为了“从边缘出
发”。
22个人的体验
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在“大江光的音乐”演奏会上的讲演。《朝日新闻》1994
年10月16日。